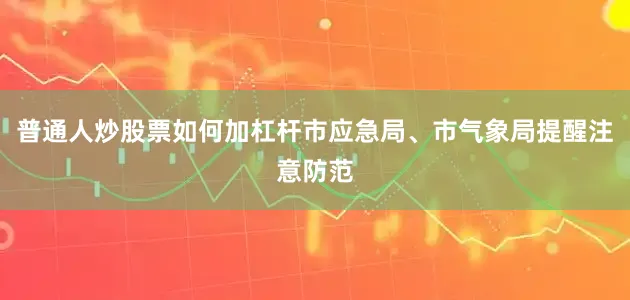“1972年1月10日14点10分,我得去八宝山。”病榻上的毛主席抬头嘟囔了一句,声音不高,却把张玉凤吓得赶紧去调车。距离追悼会开始只剩五十分钟,中南海里瞬间忙成一团。

毛主席那天穿着淡黄睡衣、腿上裹条薄毛裤,胡子拉碴,显然没有力气折腾繁琐礼仪。可他倔,硬是让工作人员在袖口缠了黑纱,扶着就往门口走。门外北风卷着细尘,吴旭君追上前替他披上呢大衣,扣子还没来得及系。
车子驶出新华门,保健医生不停提醒心率和血压,毛主席摆摆手:“陈毅跟我出生入死几十年,他走了,我不去,心里过不去。”话说得直白,带一点老人特有的闯劲。
礼堂内花圈林立,周总理、朱德、李先念等人早已等候。毛主席落座不到两分钟,便侧头询问:“张茜来了没有?”张茜身着国防绿罩衣,脸色灰白,一见主席,鼻子一酸,几乎站不稳。毛主席握住她的手,用浓重湘音压低嗓子:“节哀,你身体也不好,坐下歇一歇。”

话音未落,他又追问:“孩子们呢?快叫他们进来,我替陈毅说两句话。”四个年轻人鱼贯而入,神情局促。毛主席环视一圈,语速很慢:“你们爸爸打了半辈子仗,立下大功。这些事别当故事听,将来要顶起来。”末了,他补上一句土话,“二十年后再翻跟头,才能真懂事。”
为什么非得对这几个孩子嘱托?答案得从陈毅那段跌宕经历说起——

1901年初秋,四川乐至张安井村,陈家添了个胖娃。没人想到,这孩子15岁就跑到成都念甲种工业学院,20岁只身赴法勤工俭学。巴黎街头的冷风吹不灭他的火气,他写信和蔡和森讨论社会主义,从此顺着邮路把自己拐进了共产党。
1927年春,陈毅在湘南举起义旗,随后担任红四军师长。两年后,他被推到红四军前委书记的位置,事实上代替了因“建军路线之争”暂时失势的毛泽东。那场内部风波让外界看笑话,可陈毅没落井下石。1930年红军梅县失利后,他第一个主张“毛泽东还是要请回来”,写下著名的“九月来信”。
1934年秋,正是第五次反围剿最吃紧的节点,陈毅在江西前线腹部中弹,情势危急。红军准备长征,周恩来硬是拆开打包好的医疗器械,为他临时开刀。待陈毅苏醒,大部队已远去,他只得留下转入游击。三年光景,他率区区数千人顶着十几万敌军层层搜剿,白天猫进深山,夜里强行军。没有他,那片根据地恐怕早成焦土。

时针拨到1940年,黄桥小镇硝烟滚滚,陈毅带着粟裕的江南指挥部一把火烧掉顽军王牌,打出了新四军威风。再往后,孟良崮让“王牌中的王牌”匆匆收场;1949年,他面前摆的却是一座巨型“瓷器店”——上海。陈毅对部下说:“要抓老鼠,不砸瓷器。”于是步兵贴身肉搏,炮弹压着用,结果二十天解决战斗,外滩一片灯火。汤恩伯仓皇出海,15万守军交了枪,金融中心连一台纺织机都没动。
上海解放后,中央让他当市长。按照规定,转业干部不列入元帅评定。周总理不同意:“论资历、论战功,他缺哪一条?”毛主席想了想:“好,就破个例。”1955年9月27日,十三颗元帅星里加上陈毅。那天授衔礼结束,他悄悄跟许世友开玩笑:“本来想穿中山装,被硬塞进这身呢。”许世友笑得直拍大腿。

1965年9月的外交部记者会,再次显出陈毅的锐。港媒记者问美国借香港之地搞越南战争补给,他摘墨镜,摔在桌面:“别打主意,中国见招拆招。要打?明天来。”底气直接,翻译都跟着提高八度。同席的外媒记者咂舌:中国这位部长不像官员,更像前线司令。
可就是这位“前线司令”,1972年初倒在病榻,再也没站起来。噩耗传来,毛主席陷进被褥,足足沉默了半小时。身边工作人员说,当时屋里能听到他长长叹气。
追悼会上,周总理宣读600余字悼词,声音几次发抖。毛主席三鞠躬后,盯着陈毅遗像足足站了两分钟,才被劝回休息室。有人注意到,他袖口那条黑纱被泪水打湿,颜色深出一块。

送别结束,礼堂外北风更紧。毛主席登车前回头瞥了孩子们一眼,再次叮嘱“好好读书、勤练身体”。车尾灯消失在长街尽头,剩下的,只剩呼啸风声。那一刻,许多人突然意识到:没有长征履历的陈毅,已与共和国历史融到一起,别无二分。
名鼎配资-个人股票配资-重庆配资网-股票低息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安庆股票配资服务区内安装了7个新能源车辆充电桩
- 下一篇:没有了